
① 夏歡進(jìn)行古蛋白采樣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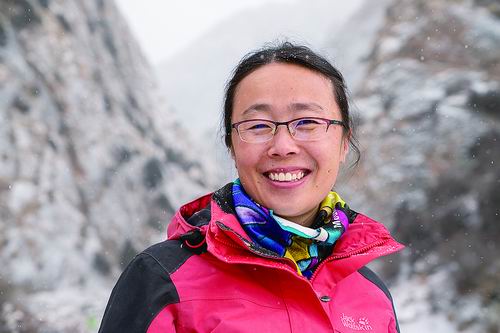
② 張東菊在野外。

③ 張東菊?qǐng)F(tuán)隊(duì)成員王建進(jìn)行動(dòng)物考古學(xué)分析�。受訪(fǎng)者供圖
■本報(bào)記者 葉滿(mǎn)山 通訊員 曲倩倩
時(shí)至今日,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教授張東菊都忘不了���,她所在團(tuán)隊(duì)研究的一件古人類(lèi)下頜骨化石被確定為丹尼索瓦人化石時(shí)���,內(nèi)心涌起的激動(dòng)之情——她漂亮地完成了多年前導(dǎo)師、中國(guó)科學(xué)院院士陳發(fā)虎交給自己的任務(wù)����。
2019年,由陳發(fā)虎領(lǐng)導(dǎo)的蘭州大學(xué)環(huán)境考古團(tuán)隊(duì)牽頭在《自然》發(fā)表了夏河人下頜骨化石的研究成果���。該化石將史前人類(lèi)在青藏高原活動(dòng)的最早時(shí)間從距今約4萬(wàn)年前推至距今至少16萬(wàn)年�,首次從考古學(xué)上驗(yàn)證了丹尼索瓦人曾生活在東亞地區(qū)的假說(shuō)。
作為一種目前基本可以確認(rèn)曾廣泛分布于東亞地區(qū)的古人類(lèi)��,丹尼索瓦人已成為我國(guó)考古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一個(gè)重要名詞����。但很多人并未注意到,發(fā)現(xiàn)這一成果的團(tuán)隊(duì)并非來(lái)自國(guó)內(nèi)著名考古強(qiáng)校����,而是在地球科學(xué)研究方面實(shí)力雄厚的蘭州大學(xué)。
這支根植于蘭州大學(xué)地理學(xué)的環(huán)境考古團(tuán)隊(duì)���,成員來(lái)自考古學(xué)����、地理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、地質(zhì)學(xué)��、生物學(xué)等多個(gè)學(xué)科。然而��,就是這樣一群“跨界”的老師�����,卻帶領(lǐng)學(xué)生發(fā)現(xiàn)了塵封16萬(wàn)年的丹尼索瓦人化石。
跨界起點(diǎn):考古學(xué)到地理學(xué)的跨越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考古學(xué)往往與田野挖掘����、古墓探秘聯(lián)系在一起����。然而在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�����,這種場(chǎng)景卻被各類(lèi)先進(jìn)的實(shí)驗(yàn)室����、精密的儀器所取代����。在這里,傳統(tǒng)觀念與現(xiàn)代科技形成鮮明對(duì)比,甚至讓人覺(jué)得有些“不協(xié)調(diào)”�。
對(duì)于這種“不協(xié)調(diào)”,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��、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教授楊曉燕很理解��。在她看來(lái)���,他們就是要站在不同學(xué)科的角度解讀考古發(fā)掘出來(lái)的各種材料�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以人地關(guān)系為核心的地理學(xué)而言����,就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天地和更遙遠(yuǎn)的過(guò)往——人類(lèi)與自然環(huán)境之間的“愛(ài)恨情仇”���。
這就是“環(huán)境考古”����。
“環(huán)境考古的核心在于探討過(guò)去的人地關(guān)系��,即人類(lèi)如何適應(yīng)���、利用和改造自然環(huán)境����,以及這些環(huán)境變化如何反作用于人類(lèi)社會(huì)。”楊曉燕告訴《中國(guó)科學(xué)報(bào)》�,環(huán)境考古更側(cè)重于通過(guò)遺存解讀人類(lèi)與環(huán)境的互動(dòng)歷史。
很顯然���,這是從社會(huì)科學(xué)與自然科學(xué)這兩個(gè)傳統(tǒng)學(xué)科中生長(zhǎng)出的新學(xué)科分支���。它在蘭大“萌芽”的時(shí)間并不長(zhǎng)——上世紀(jì)90年代,陳發(fā)虎在蘭大地理系開(kāi)設(shè)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方向��,并培養(yǎng)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��。
彼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國(guó)內(nèi)考古學(xué)仍以歷史學(xué)框架下的文化序列建構(gòu)和器物類(lèi)型分析為主導(dǎo)����,研究集中在遺址時(shí)代����、器物譜系和文化分期上�����,難以回答人類(lèi)活動(dòng)與自然環(huán)境協(xié)同演化的深層機(jī)制問(wèn)題����。在此背景下����,一些地理學(xué)和地質(zhì)學(xué)領(lǐng)域科學(xué)家開(kāi)始推動(dòng)中國(guó)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。陳發(fā)虎憑借其自然地理學(xué)背景�,敏銳意識(shí)到了這一新動(dòng)向。
只不過(guò)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在蘭州大學(xué)龐大的校內(nèi)科研體系中,陳發(fā)虎團(tuán)隊(duì)關(guān)注人地關(guān)系研究的只有寥寥數(shù)人��;而在千里之外的河北����,正上高中的張東菊還在為大學(xué)夢(mèng)伏案苦讀。
2000年高考�����,張東菊考入山東大學(xué),并意外被調(diào)劑到考古學(xué)專(zhuān)業(yè)����。這讓對(duì)考古幾乎沒(méi)啥概念的她始料未及。她猜測(cè)����,這個(gè)專(zhuān)業(yè)可能像那些玄幻電視劇一樣“有意思”。
事實(shí)與想象稍有偏差——考古學(xué)并不“玄幻”��,但同樣充滿(mǎn)吸引力�����。于是��,她從零開(kāi)始學(xué)習(xí)考古學(xué)���,踏上了這條全新道路。
只不過(guò)��,在這條路上����,張東菊的探索從一開(kāi)始就有些“不守規(guī)矩”����。
“大三時(shí)����,我經(jīng)歷了考古實(shí)習(xí)。”據(jù)她回憶���,那時(shí)�,每位同學(xué)要各自負(fù)責(zé)一個(gè)5×5平方米的探方發(fā)掘����。正是在這次發(fā)掘過(guò)程中,她第一次體會(huì)到了地理學(xué)的重要性�����。
“我發(fā)現(xiàn)土層的形成和變化記錄了古代自然環(huán)境的信息����,這些信息對(duì)于解讀埋藏其中的考古遺存至關(guān)重要。”但當(dāng)時(shí)的張東菊對(duì)地球科學(xué)知之甚少����,這讓她意識(shí)到���,要想在考古學(xué)領(lǐng)域有所建樹(shù),必須補(bǔ)充地球科學(xué)知識(shí)���。
這次實(shí)習(xí)堅(jiān)定了張東菊從事跨學(xué)科研究的信念��。隨著相關(guān)研究興趣的增長(zhǎng)��,獲得保研資格的她����,開(kāi)始尋找能提供這種研究環(huán)境的學(xué)校和導(dǎo)師�����。巧合的是���,借助當(dāng)時(shí)蘭州大學(xué)與山東大學(xué)的一個(gè)合作項(xiàng)目���,她了解到陳發(fā)虎團(tuán)隊(duì)在環(huán)境考古領(lǐng)域的探索。“這讓我看到了跨學(xué)科研究的可能性��。”
正是這種對(duì)學(xué)科交叉的渴望�,驅(qū)使張東菊作出了一個(gè)大膽選擇——從考古學(xué)轉(zhuǎn)向地理學(xué)。
初識(shí)環(huán)境考古:一場(chǎng)跨學(xué)科的邂逅
從黃河下游的濟(jì)南到黃河上游的蘭州��;從剛剛摸到了一點(diǎn)“門(mén)道”的考古學(xué)����,到幾乎完全陌生的地理學(xué),張東菊的這場(chǎng)“逆流”讓很多人不理解���。
“蘭州大學(xué)有悠久的地球科學(xué)研究歷史和雄厚基礎(chǔ)�����,這為環(huán)境考古學(xué)的發(fā)展提供了得天獨(dú)厚的條件���。我希望通過(guò)跨學(xué)科研究,更全面地揭示古人類(lèi)與自然環(huán)境間的相互作用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�。”她解釋說(shuō)����。
不過(guò)����,張東菊也有一些“不理解”�,這是導(dǎo)師陳發(fā)虎帶來(lái)的。
“剛到蘭州大學(xué)����,陳老師就交給我一個(gè)極具挑戰(zhàn)性的課題:探討‘現(xiàn)代人起源和擴(kuò)散’這個(gè)學(xué)術(shù)界未解之謎。”她說(shuō)����。
這個(gè)課題一度讓張東菊陷入了深深的迷茫——要解決問(wèn)題,人類(lèi)化石���、石器等研究材料以及相關(guān)專(zhuān)業(yè)技術(shù)等的支撐必不可少����,而作為考古學(xué)專(zhuān)業(yè)的學(xué)生����,所有材料都要從零積累,相關(guān)技術(shù)也要從零學(xué)起��。這意味著她不但要走出校園尋找遺址,還要不斷摸索合適的研究方法�。
這正是陳發(fā)虎希望看到的。
事實(shí)上��,從當(dāng)初那個(gè)關(guān)注人地關(guān)系研究的小團(tuán)隊(duì)誕生之初�,學(xué)科交叉的基因就已深植于團(tuán)隊(duì)的發(fā)展進(jìn)程中����。在這里,地理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、考古學(xué)�、地質(zhì)學(xué)、生物學(xué)等多學(xué)科深度融合�����,環(huán)境考古學(xué)科作為新興研究方向逐步形成����,這一切都需要初來(lái)乍到的張東菊快速適應(yīng)。
除學(xué)科方面外���,張東菊固有的文科思維模式也給她帶來(lái)不少困擾��,甚至因此被導(dǎo)師批評(píng)“思想保守”����。上學(xué)期間,陳發(fā)虎花費(fèi)了大量精力改變她的想法和理念��。
從文科到理科�,思維方式和寫(xiě)文章的習(xí)慣都存在巨大差異。
以寫(xiě)文章為例�����,受文科思維影響的張東菊寫(xiě)作速度較慢��,傾向于先積累知識(shí)和想法���,在保證觀點(diǎn)正確前�����,不輕易動(dòng)筆�����。陳發(fā)虎卻認(rèn)為����,科研本就是一個(gè)進(jìn)步的過(guò)程,在當(dāng)前階段����,若沒(méi)有更好的解釋?zhuān)皶r(shí)發(fā)表階段性研究成果對(duì)國(guó)內(nèi)外同行也會(huì)有啟發(fā),待有新認(rèn)知時(shí)再作更新����。
此外����,相比于可借助導(dǎo)師手把手指導(dǎo)而快速進(jìn)步的傳統(tǒng)學(xué)科研究生,張東菊只能像無(wú)頭蒼蠅一樣四處碰壁����。
“挑戰(zhàn)確實(shí)不少。”她感慨道�����,“從純粹的文科背景轉(zhuǎn)向理科��,需要補(bǔ)充大量地球科學(xué)和生物學(xué)知識(shí);當(dāng)時(shí)的蘭大也沒(méi)有專(zhuān)門(mén)的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方向�����,我需要在全新環(huán)境中摸索前行�。”
幸運(yùn)的是,導(dǎo)師給了她很大的支持和自由����,使她能自由探索方法解決問(wèn)題。在此過(guò)程中����,張東菊通過(guò)廣泛閱讀文獻(xiàn)、參加講座和研討會(huì)���,逐漸構(gòu)建起自己的知識(shí)體系�。
在張東菊于“碰壁”中不斷成長(zhǎng)的那些年��,蘭大環(huán)境考古學(xué)科也在快速發(fā)展����,而促使這種成長(zhǎng)的仍是不同學(xué)科間的碰撞與融合。
2007年���,陳發(fā)虎指導(dǎo)的第一個(gè)考古學(xué)背景的環(huán)境考古方向博士生畢業(yè)���;兩年后�����,蘭州大學(xué)西部環(huán)境與氣候變化研究院成立���,西部環(huán)境教育部重點(diǎn)實(shí)驗(yàn)室環(huán)境考古分支實(shí)驗(yàn)室建設(shè)完成。2015年�����,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和西部環(huán)境與氣候變化研究院實(shí)施合并重組���,推動(dòng)地學(xué)與考古學(xué)交叉研究進(jìn)入新階段。
此后�����,該團(tuán)隊(duì)陸續(xù)獲批多個(gè)科研平臺(tái)�����。這些平臺(tái)的接力建設(shè)持續(xù)強(qiáng)化了其環(huán)境考古領(lǐng)域的學(xué)科優(yōu)勢(shì)和研究特色。
“年代測(cè)定離不開(kāi)第四紀(jì)地質(zhì)學(xué)��,骨骼形態(tài)分析離不開(kāi)人類(lèi)學(xué)和動(dòng)物考古學(xué)��,石器分析離不開(kāi)考古學(xué)���,古蛋白解析離不開(kāi)分子生物學(xué)技術(shù)����,這些分析在我們團(tuán)隊(duì)和實(shí)驗(yàn)室都能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”張東菊說(shuō)����。
人才培養(yǎng):寬口徑、厚基礎(chǔ)�����、跨學(xué)科
伴隨著學(xué)科的快速發(fā)展����,張東菊完成了博士論文研究�,并在此期間以訪(fǎng)問(wèn)學(xué)者的身份先后赴美國(guó)���、德國(guó)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。2010年,她畢業(yè)后選擇留在導(dǎo)師的團(tuán)隊(duì)���,成為了一名老師��。
或許是自己的科研經(jīng)歷有著太多“跨越”��,初為人師的張東菊很注意對(duì)學(xué)生跨學(xué)科能力的培養(yǎng)��。正如她在受訪(fǎng)時(shí)所說(shuō)��,“我希望能培養(yǎng)既具備扎實(shí)考古學(xué)基礎(chǔ)又掌握地球科學(xué)等自然科學(xué)知識(shí)和方法的復(fù)合型人才”。
楊曉燕也告訴記者���,團(tuán)隊(duì)鼓勵(lì)學(xué)生廣泛涉獵不同學(xué)科的知識(shí)����,培養(yǎng)他們的跨學(xué)科思維和創(chuàng)新能力�����。“在課程設(shè)置上,我們注重文科與理科的融合����,讓學(xué)生既學(xué)習(xí)考古學(xué)、歷史學(xué)等人文社科課程��,也學(xué)習(xí)地球科學(xué)��、生物學(xué)等自然科學(xué)課程���。”
“團(tuán)隊(duì)設(shè)計(jì)了一套多學(xué)科融合的課程體系����。”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夏歡介紹說(shuō)��,在這套體系中�,學(xué)生不僅要學(xué)習(xí)考古學(xué)、地球科學(xué)���、生物學(xué)等基礎(chǔ)課程�����,還要參與各種實(shí)踐項(xiàng)目和國(guó)際合作��。例如���,通過(guò)參與遺址發(fā)掘項(xiàng)目����,學(xué)生可以親身體驗(yàn)地層學(xué)和考古學(xué)的實(shí)際操作�;通過(guò)參與國(guó)際合作項(xiàng)目,學(xué)生可以與國(guó)際學(xué)者共同探索環(huán)境考古的新領(lǐng)域�����。
夏歡正是這一培養(yǎng)體系的鮮活例證��。
作為陳發(fā)虎和張東菊共同指導(dǎo)的博士����,夏歡本科攻讀的是自然地理學(xué),研究生階段則將環(huán)境考古作為研究方向����。最終�,她在古蛋白質(zhì)組學(xué)領(lǐng)域形成獨(dú)特優(yōu)勢(shì)�,其研究成果已成功應(yīng)用于多個(gè)研究項(xiàng)目����,并獲得了業(yè)內(nèi)廣泛的引用與參考。
“對(duì)于我們這個(gè)涉及多學(xué)科交叉的領(lǐng)域�����,單一學(xué)科很難真正解決問(wèn)題��,只有對(duì)所涉及學(xué)科都有深刻認(rèn)識(shí)��,才能有機(jī)融合多學(xué)科的研究結(jié)果���,講出完美的‘故事’��。”如今已經(jīng)成為教授的夏歡說(shuō)����。
為了講好這些“故事”��,該團(tuán)隊(duì)每年野外工作時(shí)間長(zhǎng)達(dá)3~5個(gè)月���,發(fā)掘工作都由師生親手完成��。“我們要自己去發(fā)掘自己研究的樣品���,這樣才能清楚它的出土情況���,明白它能解決什么考古學(xué)問(wèn)題,然后在實(shí)驗(yàn)室利用自然科學(xué)手段進(jìn)行分析���,這樣對(duì)數(shù)據(jù)的解釋才會(huì)有據(jù)可依���,不會(huì)脫離考古學(xué)背景。”楊曉燕說(shuō)���。
在從事科研工作的同時(shí)��,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還利用自身學(xué)術(shù)資源和人脈關(guān)系��,為學(xué)生爭(zhēng)取實(shí)踐項(xiàng)目和合作機(jī)會(huì)��。借此����,學(xué)生可以參與團(tuán)隊(duì)的大型科研項(xiàng)目,負(fù)責(zé)數(shù)據(jù)采集和分析工作�����;也可以參與國(guó)際合作項(xiàng)目����,與國(guó)外學(xué)者共同開(kāi)展研究����。這些實(shí)踐機(jī)會(huì)不僅提升了學(xué)生的專(zhuān)業(yè)能力,也增強(qiáng)了他們的團(tuán)隊(duì)協(xié)作和溝通能力����。
學(xué)術(shù)氛圍:鼓勵(lì)創(chuàng)新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
如果說(shuō),對(duì)于學(xué)生的跨學(xué)科培養(yǎng)是培育一株幼苗的話(huà)���,那么包裹在幼苗周?chē)?ldquo;營(yíng)養(yǎng)液”����,則是團(tuán)隊(duì)內(nèi)部開(kāi)放包容的學(xué)術(shù)氛圍��。
“良好的學(xué)術(shù)氛圍對(duì)于跨學(xué)科研究至關(guān)重要�����。”楊曉燕表示,團(tuán)隊(duì)特別注重營(yíng)造開(kāi)放����、包容、創(chuàng)新的學(xué)術(shù)氛圍��。
對(duì)此�����,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�、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教授董廣輝解釋道,團(tuán)隊(duì)鼓勵(lì)學(xué)生提出不同的觀點(diǎn)和想法��,尊重每個(gè)人的學(xué)術(shù)興趣和研究方向���,同時(shí)注重培養(yǎng)學(xué)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創(chuàng)新能力���,鼓勵(lì)他們勇于挑戰(zhàn)傳統(tǒng)觀念和方法。
“為營(yíng)造這種氛圍�,我們定期舉行學(xué)術(shù)研討會(huì)和講座,邀請(qǐng)國(guó)內(nèi)外知名學(xué)者來(lái)校交流���;我們還鼓勵(lì)學(xué)生參加國(guó)際學(xué)術(shù)會(huì)議和合作項(xiàng)目����,拓寬他們的學(xué)術(shù)視野和交流能力。”他說(shuō)�。
在這方面���,讓博士生李源新印象最深刻的是團(tuán)隊(duì)的每周例行組會(huì)�。
“組會(huì)上�����,不管是博士生��、碩士生��,還是剛?cè)霂熼T(mén)的本科生��,都可以暢所欲言����,提出質(zhì)疑或建議。”李源新告訴《中國(guó)科學(xué)報(bào)》��,不管是誰(shuí)匯報(bào),張東菊都會(huì)隨時(shí)詢(xún)問(wèn)“大家有沒(méi)有聽(tīng)懂”��,這種鼓勵(lì)提問(wèn)和討論的方式營(yíng)造了良好的學(xué)習(xí)環(huán)境���,即使學(xué)生被問(wèn)得“語(yǔ)塞”����,也不會(huì)受到批評(píng)���。
對(duì)此����,張東菊解釋說(shuō):“我現(xiàn)在問(wèn)學(xué)生的問(wèn)題越多��,他們懂得就越多�����,功底就越扎實(shí)�����,他們畢業(yè)答辯時(shí)就會(huì)越從容��。”
從陳發(fā)虎播下的環(huán)境考古種子,到如今在丹尼索瓦人研究�、高原農(nóng)牧業(yè)傳播、古人類(lèi)的高海拔適應(yīng)機(jī)制等領(lǐng)域結(jié)出的碩果����,如果將蘭州大學(xué)環(huán)境考古團(tuán)隊(duì)比作一位寒窗苦讀多年的學(xué)生,在張東菊的眼中��,這名有了如此成績(jī)的“學(xué)生”���,是否可以“從容答辯”了呢?
張東菊的回答意味深長(zhǎng):“成果代表了過(guò)去�����,也是新的起點(diǎn)��,未來(lái)真正的挑戰(zhàn)在于如何讓交叉學(xué)科‘活’下去�����、‘長(zhǎng)’起來(lái)�。”
她告訴《中國(guó)科學(xué)報(bào)》,當(dāng)前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方向在多個(gè)高校已陸續(xù)成長(zhǎng)起來(lái)�,均呈現(xiàn)出多學(xué)科交叉融合���、國(guó)際合作深化及服務(wù)國(guó)家戰(zhàn)略的特征。
具體而言���,傳統(tǒng)考古學(xué)強(qiáng)校通過(guò)新加入的地質(zhì)學(xué)手段輔助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���,以地質(zhì)與地理學(xué)科為優(yōu)勢(shì)學(xué)科的部分院校則依靠自身優(yōu)勢(shì),通過(guò)構(gòu)建跨學(xué)科團(tuán)隊(duì)����、搭建國(guó)際合作平臺(tái)等方式,推動(dòng)環(huán)境考古從區(qū)域特色研究向全球?qū)W術(shù)引領(lǐng)跨越����。
“環(huán)境考古正在突破傳統(tǒng)考古學(xué)‘就物論物’的局限,將研究視野擴(kuò)展至人類(lèi)活動(dòng)與自然環(huán)境的動(dòng)態(tài)互動(dòng)�����。”張東菊表示�,這一范式轉(zhuǎn)型也推動(dòng)考古學(xué)從“文化史研究”向“社會(huì)過(guò)程研究”轉(zhuǎn)變。
比如��,張東菊帶領(lǐng)團(tuán)隊(duì)在青藏高原開(kāi)展了大量考古調(diào)查與發(fā)掘,他們不只想重建古人類(lèi)向高原擴(kuò)散的時(shí)空過(guò)程��,更希望理解這背后的機(jī)制��,特別是不同人群對(duì)高海拔環(huán)境適應(yīng)的機(jī)制�����。去年��,他們?cè)凇蹲匀弧钒l(fā)表了丹尼索瓦人在高原上對(duì)多樣性動(dòng)物資源進(jìn)行充分利用的研究成果��,這是回答丹尼索瓦人如何適應(yīng)高海拔環(huán)境問(wèn)題的重要進(jìn)展���。
在這一過(guò)程中,交叉學(xué)科團(tuán)隊(duì)的重要性愈加凸顯����。
張東菊表示,任何一個(gè)學(xué)科團(tuán)隊(duì)的成長(zhǎng)都會(huì)經(jīng)歷風(fēng)雨���,交叉學(xué)科團(tuán)隊(duì)要想穩(wěn)健發(fā)展�,關(guān)鍵在于搭建“營(yíng)養(yǎng)豐富”的生態(tài)平臺(tái)——既要有如陳發(fā)虎這樣兼具多學(xué)科經(jīng)驗(yàn)和國(guó)際視野的帶頭人����,也要有專(zhuān)門(mén)的協(xié)同辦公空間與實(shí)驗(yàn)平臺(tái)���,讓不同背景的人才及時(shí)交流、無(wú)縫合作���。
“交叉學(xué)科的核心是‘人’�����,沒(méi)有包容的政策和多元的人才池��,再好的想法也會(huì)枯萎����。”楊曉燕說(shuō)���。
值得一提的是���,當(dāng)前環(huán)境考古作為考古學(xué)與地球科學(xué)、環(huán)境科學(xué)等學(xué)科的交叉領(lǐng)域��,已在國(guó)內(nèi)形成較為系統(tǒng)的研究框架�����,并打破傳統(tǒng)考古學(xué)的局限,讓考古學(xué)在理科學(xué)院中煥發(fā)出新的生機(jī)����。
“如今,考古學(xué)早已擺脫了單純的文科研究范式����,與多學(xué)科深度融合,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范式����。”楊曉燕說(shuō),這不僅拓寬了考古學(xué)的研究視野��,還為解決傳統(tǒng)考古學(xué)難題提供了新思路�����。
“從這個(gè)角度看����,考古學(xué)已經(jīng)不再是一個(gè)‘冷門(mén)’專(zhuān)業(yè)了���。”張東菊笑著說(shuō)���。

蘭州大學(xué)資源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師生在考古遺址發(fā)掘現(xiàn)場(chǎng)��。受訪(fǎng)者供圖
《中國(guó)科學(xué)報(bào)》 (2025-08-19 第4版 高教聚焦)